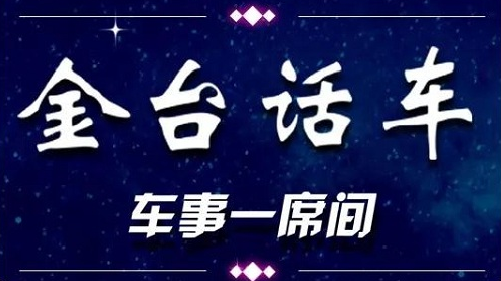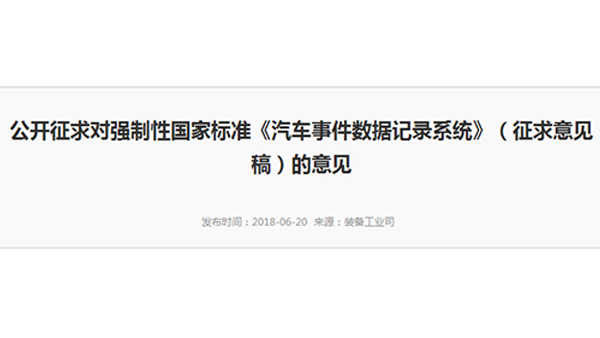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发改委”)向业内各有关部门发布的《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经本报第一时间解读后,在行业内迅速引发震动。伴随着持续不断的热议,新规中的矛盾点和争议点也逐渐显现。
6月12日,《中国汽车报》大型直播访谈节目——《金台话车》之“投资新规要来,汽车业准备好了吗”邀请了4位业内专家就《意见稿》涉及到的焦点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由右至左依次为:王晓明、安庆衡、王小广、赵英、韩忠楠
♦嘉宾: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委员会主任 安庆衡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发展室主任 赵英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 王晓明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研究员 王小广
♦主持人:《中国汽车报》社全媒体采访中心记者 韩忠楠
♦并非“第三版产业发展政策”
《中国汽车报》:各位专家在接到《意见稿》后,最大的感想是什么?这份投资管理新规被不少业内人士解读为中国汽车行业的“第三版产业发展政策”,对此各位认同吗?

赵英:首先,投资管理新规是国家根据国内外大形势和我国汽车工业技术革命现状做出的适时调整,但这不意味着它就是第三版的产业发展政策,后者涵盖的内容要细致的多。但是《意见稿》依然是一个重大的产业政策,是对以前产业政策的重大变革,意味着我国的汽车产业政策发生的巨大变化。它透露的另一个重要信号是,政府可能不会再出台类似以前那种面面俱到、无微不至的产业政策,而是由过去的全盘干预和全面管理,转向为在准入门槛和重大技术经济政策上的重点管理。仔细研读《意见稿》,还是发现一些值得商榷之处。比如新规把混合动力汽车归类到了传统燃油车,而我认为混合动力是个很好的过渡产品,不能通过强制手段进行干预。国家对于以往产业政策进行变革非常必要,但《意见稿》中仍存在管理过细之处,需要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行政干预。

王小广:把投资管理规定定义为“新规”比较准确,但它决不是整个行业的产业政策,而只是产业政策的一部分。新规出台有两大背景:一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强国总目标中,制造强国是12个强国子目标的第一个,而在制造强国里,汽车强国显然是最重要和最核心的。中国汽车产业当前的突出问题在于自主创新,按照我国当下的汽车总体量,不应该一个世界级品牌都没有;二是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宣布中国将继续扩大开放,其中特别强调了汽车业,新规其实是对国内外开放大背景的呼应。在内容上,《意见稿》体现了两个很好的倾向。其一是放开准入和下放权力两大意图。准入向有实力的民营资本、社会资本放开很有必要,放权到地方的大方向也是没问题的;其二是要通过结构调整来解决中国汽车产业面临的问题,要盘活存量而不再依靠增量。具体到新能源汽车,近段时间,我们在技术路线上明显感觉到一种纠偏的意味,我认为未来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一定是多元化的路径,而不能是单项的方向。总体来看,尽管在行业发展的战略层面考量得不够,但新规体现的总方向是对的。

安庆衡:新政主要体现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整顿,一是改革。中国汽车工业面临着诸多挑战,相应的国家主管部门也面临不少挑战,比如此前发改委批复的15家企业就颇具争议。因此新规里调整和改革的氛围比较浓。比如整顿僵尸企业,打击投机投资等,对于治理汽车行业当前存在的问题,对于解决新能源汽车一哄而上的问题,肯定是有效的。但这里面整顿的意味过浓,管理的力度过大,推动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气氛就少了,这二者如何平衡是需要研究和细化的。另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是,《意见稿》强调的放权地方政府在真正落实上会很困难,发改委、工信部和地方之间如何协调,哪些权力下放,哪些不下放等,需要仔细落实。总之,新政的方向和精神都是对的,但是开放得还不够,需要落实的地方很多。另外,对于推动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的初衷不见得实现那么好。

王晓明:此前两版汽车产业发展政策是战略层面的,此次的新规更多在执行层面,它不具备稳定性和连续性,并且根据形势发展随时可以调整。因此新规肯定不是第三版的产业发展政策,二者不在一个层面上。《意见稿》更多是从工作导向和问题导向出发的。一方面,它是国务院已经出台的《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在汽车产业领域的工作细则,也是落实国务院“放管服”改革、下放审批权的工作需要;另一方面,它是为了解决股比放开、新能源汽车产能过剩、僵尸车企等行业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放到汽车产业管理体制的长线来看,这一版新规虽然还是事前管理,但它可以看作是国家对于汽车工业的管理由事前管理向事中和事后管理转型的一个中间衔接点,此前带有计划经济和行政色彩的产业政策在这一版到了尾声,未来将转向以统一市场、开放竞争为目的的事中和事后管理。
♦整顿意味过浓 开放氛围不足
《中国汽车报》:既然大家认为,《意见稿》在审批权下放和准入门槛上有一定的矛盾点,能否具体谈谈?对于解决矛盾是否有比较好的建议?

赵英:我的理解很简单。既然国家已经把基本的技术、环保和投资门槛设置的比较严格,也已经把权力下放到地方,那么其他的不必约束太多。后续各省、各地方按照国家的新规定来进行审批即可,主管部门没必要再从各个省份进行划分。那些工业基础发达、新能源发展较好较快的省份自然会走在前面,类似产量、充电桩等的要求完全可以省略。
王小广:这其中的矛盾点很多。放权到地方后,各地方政府在进行审批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连续两年新能源汽车产量占比高于行业平均水平,这个标准如何认定?是不是最终还是要工信部和发改委来制定?因此,放权到底怎么放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如果在技术标准、环保标准之外,再在金融等各个方面都设置约束,那这个政策就不是一种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或是产业政策了,而是一种紧箍咒性质的约束标准。
安庆衡:我建议把下放审批权和考察地方水平两件事情结合起来。新创企业的投资者在省份选择上本身是有考量的,地方政府也会研究项目的可行性。落实审批权下放,给予地方政府更大权限,有利于地方汽车产业的长远发展。
王晓明:放权地方在执行层面会存在很多问题,拿捏地区之间的平衡很不容易。此前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很多僵尸企业就是因为地方政府与企业投资紧密捆绑而产生的。按照新规要求,极有可能出现一种现象:地方政府在消灭一批僵尸企业的同时又产生了一批新的僵尸企业。此外,地方政府还存在的“前朝不理旧政”现象,也会为建设风清气正、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带来一定干扰。当前,产业投资的一窝蜂现象,和新造车企业的良莠不齐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必然,最终的淘汰应该由市场来选择,我不赞同过多的行政干预。放权地方并不能解决前置性审批的本质性问题,应该减少这种行政干预,把对汽车行业的管理重点转移到建立起事中和事后管理体系上。
♦决定新造车企业命运的是市场
《中国汽车报》:很多业内人士都认为《意见稿》提升了新能源汽车投资门槛,将有效打击投机行为,令很多新造车企业难眠。新规对于新造车企业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赵英:新规并不是针对所谓新造车势力的,在挑战面前,无论新旧。但是我想借此机会应该提醒一下新造车企业:汽车是一点一点造出来的,产品质量、生产线、供应商、技术团队等等都需要打磨,如果不尊重汽车工业的发展规律,那么新造车企业的生存概率将非常小。
王小广:门槛提高是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技术角度来看,新规提出的技术标准并不算高。现在主要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我们的汽车补贴政策还需要调整,朝着打击投机、提升技术的方向调整;二是技术标准还需要强化,比如研发占比高于3%的门槛设置在汽车业根本不算高标准,我们要想建立世界一流的汽车企业,现在的这个标准还远远不够。
安庆衡:新规对于新造车企业提了很多新要求,但它对于现在的造车新势力并不是一种挑战,现在的门槛更多是为了挡住那些无序竞争。对于当前已经获批的或是已经进入汽车行业的新造车企业,我认为虽然新规对他们影响很大,但是下一步市场对他们的反应更为关键。如果产品很好,消费者也认可,市场等各方面反应都很好,那么所谓门槛是挡不住其发展的。造车新势力到底怎么样,今年底或明年底,市场自然会给出结论。
王晓明:汽车行业本身就自带天然的高门槛,这个高门槛对造车新势力是很大的风险,会自然过滤掉其中的投机分子。而且我认为造车新势力不一定非要造车,它可以设计车,然后利用现有产能来帮助生产车。当前,汽车产业正处于大的产业变革的起步期,传统的产业格局已经在向链式格局转型,我们需要宽松的环境来培育和壮大新的主体。所以我认为应该给予新造车企业更多机会,至于靠不靠谱就交给市场。
♦混改将有利于世界级自主品牌诞生
《中国汽车报》:《意见稿》明确了支持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兼并重组,组建世界一流的汽车企业集团。这传递出什么信号?
赵英:我完全赞成混改。目前从机制体制上来看,汽车行业内是央企不如地方国企,地方国企又不如民营企业。但是新规关于混改的部分并不是政策发生了变化,而是在落实党的十九大以来关于国有企业混改的改革政策。尤其是在汽车业合资股比逐步放开的情况下,鼓励混改将更加有利于企业机制的转变,激发内在动力。
王小广:我总体上赞同新规中关于混改的内容,也就是通过兼并重组,通过整合和限制扩张来解决中国汽车行业相关问题。缺少世界级的品牌和企业,缺乏自主创新是当前我国汽车工业的核心问题。我在十年前就认为合资模式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自主汽车品牌的发展。现在,我们的股比要逐步放开了,政府也在鼓励兼并重组,在这样的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市场自然会形成以存量调整为主的发展方向,让强强联合或是强弱互补。放开之后,国家只需制定相关的公平合理的市场政策,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去优胜劣汰,这才是行业发展应该遵循的规则和方向。
编辑:薛亚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