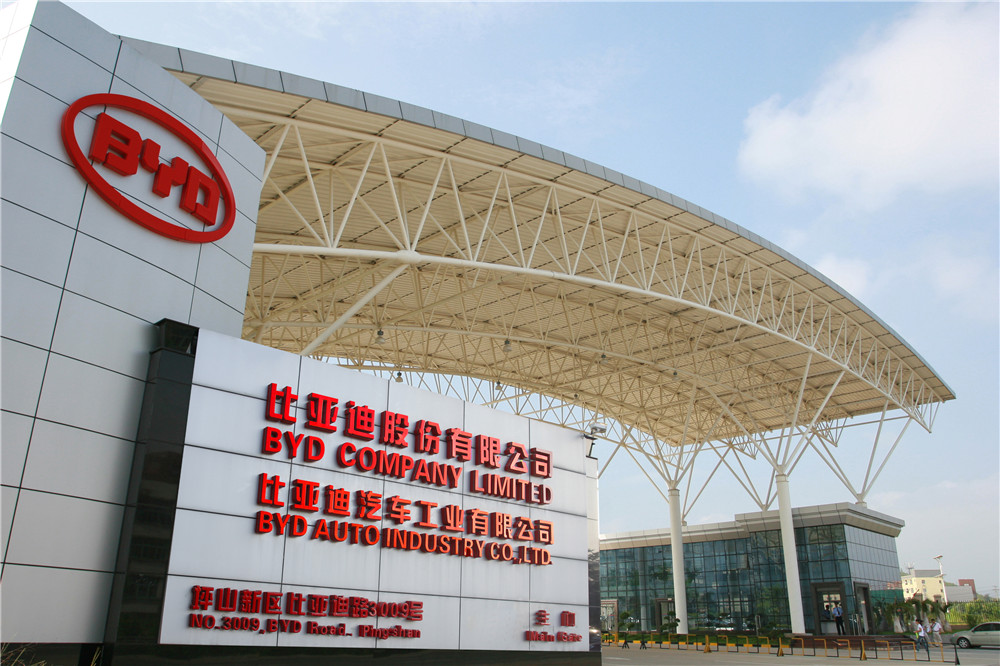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中国汽车报》创办35周年的大喜日子,我作为贵报忠诚的读者和忘年之交,也同样以十分喜悦的心情忆念这难忘的岁月。

1984年,你们创办时,归属于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那时,我们是在一个大楼里办公的,无论是你们年长的创办领导者,当时是中汽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兼任《中国汽车报》社的社长,还是年轻的记者,我们都成为朋友。我们在同一个饭堂里吃饭,能不常有接触和交流吗?1995年,你们归属机械工业部,我那时也已调到部里,创办中国汽车工业工程咨询公司,我们又在一起办公,在饭厅里相处了。
1998年,机械工业部撤销,但何光远、吕福源部长把我安排到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委员会里当秘书长。这是一批由汽车界大企业退下来的老领导和老专家组成,专门为汽车产业议大事、出主意的咨询服务性机构,受到国家和汽车界人士的关注。正好那时我国汽车产业正处在一个改革开放、合资引进的崭新的年代,要做的事情真不少。这样,使我成为一个退而不休的人士,要参与的汽车界活动也不少,特别是参加《中国汽车报》组织的活动更多些,从中得到不少新的收获和情谊。
那时,在咨询委员会里的老同志方劼对我说,现在你退下来了,对汽车界的各项新气象要多观察,多提想法,就不用像原先未退下来时那样谨慎小心了,只管说良心话,不管对和错。那时,方劼对支持民营汽车企业特别关心,他带我去浙江台州吉利汽车见李书福,带我去北京福田汽车去见王金玉,目的是推动汽车产业组织结构改革,会同国有汽车企业实行市场机制的互动和竞争,推动汽车产业更好更快的发展。
这样,我虽然退休了,但对媒体的各种活动,特别是贵报举办的研讨会、评选会、专题研讨会、专访等活动,该说的就说,是对是错不重要,都按自己体验去讲。如前两年在一次研讨会上,我发言说:“汽车零部件应该是生产出来的,而不是靠检验的。” 《中国汽车报》刊载了我的发言,引起了相当热烈的反响。因为我在日本丰田公司考察时曾看到,在汽车装配线外面有接受外供件的平台,按五分钟、半小时、半天、一天等分类,供应商按要求将零件送到不同时段的要求分类中,进行发送,到时即装上汽车,从不检查,这就是丰田生产方式的诚信管理和文化体现。这个观点,当时有上百家网站转载,至今还有不少留存着。

2017年10月,浙江最有名望的民营企业家鲁冠球去世。因为之前我们有着深厚的交往,我写了一篇纪念文章,附带几张我们相处的照片,你们用《陈光祖:追忆鲁冠球一些相当珍贵的照片故事来源》登载,引起不少民营企业家的关注。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提出要重视小型汽车的地位,让自主品牌小型汽车驶过天安门。为此,我在贵报和各网站刊发了十多篇评论。因为我还是北京市政府顾问,就到北京市政府顾问委员会办事处去反映,最终得到北京市支持。在批准通行天安门那天,我约请你们和人民网、凤凰网、搜狐网和汽车网友,在天安门专门拍照,并发表不少现场的照片。现在,据说有的城市也即将允许皮卡通行了,这是我们对汽车消费平民化理念改革的一大表现。
还有,前几年我提出“一汽和东风汽车可否合并重组”的观点及文章,得到你们的支持,包括人民网、新华网汽车版支持,都刊登了,想不到有300多万读者阅读了这篇文章,大部分是股民,使一汽、东风相关股价上涨。实际上,我不是给股民写的,目的是为了在全球化汽车激烈竞争年代,避免这两大企业的一两万工程技术人员重复劳动,合并进行严密的分工,不浪费那么多精力,可以向更高级的研发、制造、营销方向发展,建设千万级跨国汽车企业,更好地提升汽车内生的竞争力。
早在1987年,我参加一次综合性经济论坛上,发言“要在汽车产业推行国家控股为主的混合所有制公司,使国企改革能得到更好的改革和发展”。在1987年3月16日,贵报在头版头条刊登我的《汽车工业企业应当试行国家控股制》文章,引起相当热烈的反响。至今,我认为我们汽车大国企改革的一个方向,应当实行国企为主的混合股份制改革工作,也是汽车国企改革一大结构性方向。
进入21世纪,我在多次电动汽车论坛上发言,认为电动汽车发展的根本举措是建立新型的电动汽车的商业模式。在发展初期,靠国家补贴是可以的、必要的,但不能靠终身性补贴去发展,也不应是仅靠技术路线能全面解决问题,而是应该研讨结合中国国情的商业模式,才是根本出路。
在汽车产业全球化、信息化、高科技迅猛发展的情况下,一定要把汽车的芯片和操作系统工作搞好,才有自主的主动发展基础性条件,不受外在卡脖子的影响。贵报在2007年4月9日,发表我的以《芯片,汽车电子难以跨越的一道坎》的文章,之后我还从不同角度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可以说,近来我们的芯片在众多产业有不少实现了比较好的进步和发展,如在汽车产业一些车载用芯片可以了,但车控芯片及操作系统还几乎是零,全靠外资企业和进口。最近华为事件给了我们不少警示,到底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不是汽车企业自身能解决的,一定要依靠国家大力支持,在顶层设计上下苦功夫,长期规划,再也不要走一哄而上大家干的路子,要集中一切力量支持两三家企业,把芯片和操作系统的研发工作做起来。如若不然,最近我们自主品牌汽车市场占有量从过去50%降到40%,还会降。因为靠国外,依赖高价芯片,特别是车控芯片MCU、SoC的芯片,还是要把具体内容要求告诉供应商,在芯片上把软件给注入,这不是一般的缺失,还得把自己的秘密先告诉人家。
最近,我在贵报写了纪念王大珩院士致力发展汽车系统芯片的文稿。在上世纪末,中科院王大珩院士等向国家建议,要建设汽车产业的芯片工程,并邀请我和汽车大集团几个专家参与多次活动,反复研讨了两三年时间,国家将此工作交给当时电子工业部办理。那时,电子工业部忙着发展网络,没钱也没时间好好做。过了一段时间,把汽车芯片工程给忘掉了。王大珩院士多次强调,不把汽车芯片工业搞上去,中国汽车工业一定会成为“空心化”产业。
2011年,王大珩院士去世时,《科技日报》专访了我,他们还核查了报纸的资料,刊登了一篇以我的名义写的《为王大珩院士未了的心愿》的文章。贵报也在相关文稿中转载了这篇文章。汽车芯片,是很值得我们汽车人深思的一个大问题。
2018年10月29日,贵汇全文刊登我的《汽车企业应以研发而非制造为中心》的文章。这是我在华晨汽车一次研讨会上发言的内容,通过你们记者整理,在你们的报纸和网站上同时发表的。我们几十年来都是以制造工厂为中心,要让有关方面都看到,这样做的结果是对研发这个核心缺失了,不少新技术还很依赖别国的科技和进口。现在的硅谷,几乎所有的科技企业都在为汽车的新兴科技发力。我多次到硅谷参观,他们不建大楼,不穿西装,不搞实物制造,干的只是发明,特别对新能源汽车、智能汽车都从不同角度下苦功夫研发,力争能有所突破,实现“破坏性创新”。如苹果手机、iPad等,多数是在中国由富士康代工,再返销给我们的。99%利润由苹果拿去,我们可能只赚1%。所以,在新时代,汽车产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一定要以研发为中心,用新产品取代传统产品,形成新兴的市场。这个道理一定要在汽车界讲清楚。
2013年,我曾在《人民日报》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发言,提出汽车产业要以研发为中心,而非制造,就是指不是靠工厂,是“软制造”取代“硬制造”,使汽车制造业走向高端化,走向全球化。2018年12月10日,你们发表我的《汽车产业需勇闯人工智能“无人区”》的专论。简要的说,我们至今还大多对高科技只求终端、不求基础研发,只求表现、而缺乏基础理论。而最终,这样会导致我们汽车核心科技仍会不断地拉开差距。汽车智能化很重要的理论是“控制论”,但在目前众多智能化的研讨会上,几乎很少见到发表这方面意见的,这值得我们深思。
最后,我想用在2000年10月10日发表的《漫谈21世纪汽车工业的创新工程》和2000年10月23日发表的《对汽车工业国家创新系统的构想》,这两篇文稿,都是在《中国汽车报》上发表的,我们要以汽车创新工程思维和行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定要做到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解难题,抓落实。我们都老了,这只能是我们汽车老人的殷切期待,以此来寄托我们汽车产业走向强国的情怀。
在此,我想用八个字:“学自刊网·谊从媒友”,来表达我对《中国汽车报》的情感和寄托,祝《中国汽车报》越办越好,为建设汽车强国再增添“一把火”。(作者系原中国汽车工业工程咨询公司总经理、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委员)
本文由记者赵建国整理